男女主角分别是王兴逸李文凯的现代都市小说《沽河逸影全本阅读》,由网络作家“海邦书语”所著,讲述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故事,本站纯净无弹窗,精彩内容欢迎阅读!小说详情介绍:经典力作《沽河逸影》,目前爆火中!主要人物有王兴逸李文凯,由作者“海邦书语”独家倾力创作,故事简介如下:?”“是吗?可能是茶下得太俨了,俺给您老的茶杯加点水。”孙有治说着,拎起暖瓶在茶杯里倒了点水。“您老再尝尝。”杨长礼又喝了一口,砸吧几下嘴说道:“香气倒是可以,这味…”“老茶,老茶,老树上的茶,发酵过,味足,耐泡,俺老弟从南方带回来的,呵呵。”“哦,那咱继续说。”话说咱这地,安定了百十年之后,大概到明朝......
《沽河逸影全本阅读》精彩片段
讲故事的人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者,叫杨长礼,年轻的时候在外闯荡过。他家里有些早年间的书,知道很多奇闻异事。只要他在,别人都是听众。
杨长礼刚讲完一段黄鼠狼抢夺黑蛇内丹的故事,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水,准备开讲下一段的时候,一个中年男子说道:“杨老,您老讲点新鲜的故事,别总讲五仙,没尾巴老李,鬼魂,僵尸等等,这些都听了多少遍,早就听腻了。今天刚买的好茶,您老也讲点新鲜的,来点历史故事,我听说咱这里以前发生过不少大事,呵呵呵。”
中年男子叫孙有治,住在村子西边,夏天晚上乘凉的时候,得空就跑到村子东边来听杨长礼说故事。
“嗯,今天这茶味道挺冲,咱们就说点新鲜的。你们知道咱这个村的人是从哪里来的吗?”
“晋阳洪洞大槐树搬迁过来的。”
“不对啊,我怎么听说是从芸㣮迁过来的。”有人反驳道
“你们说得都对,也都不对。”杨长礼神秘的说道。
“杨老,您老就说吧,俺们都听着呢?茶水也给您换新的了。”孙有治催促道。
杨长礼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水,再点上一袋旱烟,略回味了一下,开始说了起来。
元末明初的时候,这里发生大战,人都快死绝了,朱元璋迁移人口,准备将晋阳的人迁到齐地来开荒种地,但是人们不愿意背井离乡,朱元璋就用手段强制迁移,然后就有了“要问祖上哪里来?晋阳洪洞大槐树“的说法。
祖上过来之后,开荒种地,经过多年发展,人口逐渐繁衍开来。我们老祖宗就居住在我们村子的北边,现在的北石盘村。
定居之后,人口开始增多,然后得盖新房,打地基的时候,不知挖出多少腐烂的人骨,有的区域成片都是,但是已经居住了许久,不好再搬动,也没那个精力和费用,官府那边只安置一次,再次搬动很麻烦,所以只能将人骨挖出来,安置到深沟的边缘角落里,再填土埋上,上面种树或是庄家。
期间也有一些闹鬼,走阴魂之类的事件,晚上还经常看见鬼火,大家走夜路也不得安生,后来请高人作法,又清理出很多人骨掩埋到深沟的角落里,如此之后,总算清净了一些。
“关于这些闹鬼,走阴魂,五仙之类的故事咱们明天晚上再说。”杨长礼郑重的强调道,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水,砸吧几下嘴,低头看看茶杯,又看看眼前的孙有治。
“唉,有治,这茶咋沙口这大?”
“是吗?可能是茶下得太俨了,俺给您老的茶杯加点水。”孙有治说着,拎起暖瓶在茶杯里倒了点水。
“您老再尝尝。”
杨长礼又喝了一口,砸吧几下嘴说道:“香气倒是可以,这味…”
“老茶,老茶,老树上的茶,发酵过,味足,耐泡,俺老弟从南方带回来的,呵呵。”
“哦,那咱继续说。”
话说咱这地,安定了百十年之后,大概到明朝中期的时候,又遇到新的问题,那就是倭寇入侵。
倭寇凶残,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凡是被倭寇见过的人,基本上没有活下来的,要么被杀,要么被抓到倭国为奴。
大明朝廷派出戚继光,将东南沿海的倭寇一一剿灭,倭寇损失惨重,无法再大范围的作恶,就将一部分倭寇分成小队到处流窜。我们蛟岽地区离海近,自然也受到倭寇的侵扰。
后来倭寇听说戚继光的家乡在蛟岽地区,就不断的派人打探,一边寻找,一边作恶,不断往蛟岽地区增派人手。
当时,朝廷里有宦官专权,欺上瞒下,对下面发生的一些事情都是轻描淡写,实在掩盖不住,才从芸㣮调来一些将士。
在蛟岽地区建立卫所,有卫,有所,卫大,所小,所分千户所和百户所。直到现在,蛟岽地区有些地方的名字还带卫,源远就在这里。当时,我们这里人口还少,只设百户所,没有卫所,军士大都是从当地征集而来。
第一任参将叫熊文远,也是最后一任参将,后面就没有了,因为百户所撤掉了。
他从芸㣮调过来之后,将周围地形查看了一遍,发现只有我们村子这边的沟最深,而且沟的旁边还有一块高大的巨石,稍作修整,就可以作为观察敌情的瞭望塔。所以他根据地形,将堡垒建在这边,就是我们柏前村现在的位置。
开始的时候,我们打退了一些零散倭寇的侵扰。
不多久,更多的倭寇来侵扰我们。熊文远早有准备,在周围设下埋伏,几乎全歼来犯之敌,同样,我们的人也付出不小的代价。
倭寇们虽然吃了大亏,但是也发现了我们的弱点,人少,地势平坦,相比于其它的百户所来说,更容易攻打,而且,想要继续深入内地寻仇,很难躲过瞭望塔的观察。
所以,倭寇们组织更多的人手,准备了云梯,等待时机攻下我们的百户所。
有一天朔月,刮着大风,下着大雨。深夜之时,倭寇们从小路偷偷绕过其它百户所的警戒范围,来偷袭我们,等我们的斥候发现的时候,倭寇们已经快到了。
熊文远断定这个所是保不住了,所以立刻决定,留下百人断后,每户出一人,家中是独子的不留,其他所有人护送老幼妇孺撤往后方。但是你想,我们祖宗在这百十年间一共才繁衍了多少人,以前的医疗条件可不比现在,古代能活到成年的孩子的比例很低。连皇帝家的孩子长大成年的都在一半左右,民间的更不用说了。
再加上前几次已经战死一些人,剩余的青壮年哪里能凑齐百人,只能有多少算多少,号称“百甲勇士”。
因为事情紧急,立刻就得走,晚一分钟都不行,什么财物,粮食都来不及带走。
同时,因为雨势太大,烽火通信的功效大打折扣,旗花也不敢保证能把信息传递出去,为了保证信息能够传递,熊文远派出几名斥候去附近的百户所通知调人,但是所之间的距离少说也有几十里地,再加上当天正是朔月,乌云密布,出去那是两眼一抹黑,也不敢打灯笼,只能勉强用手捂着火折子看看,还得赶紧藏起来,就这样,我们派出去的斥候还被截杀了好几个,信息送到的时候,时间已经过去了一个时辰,那边的百户所安排士兵过来救援,但是路滑难走,赶到的时候,天都快亮了。
一场血战之后,熊文远和留下的人全部战死。等其它所的人赶到的时候,倭寇已经攻下了堡垒,并洗劫了我们原来的村子,能带走的就带走,带不走的全部付之一炬,以前的房顶都是茅草,一点就着。
“杨老,不是下大雨吗!怎么会点着?”孙有治插口问道。
杨长礼喝了口茶,正要说下段的时候,被打断了话茬,不禁有些气恼。
“后生,我怎么感觉你这茶的味道不太对,好像…。”
“老茶,老茶,老树上的茶,发酵过。呵呵呵。”孙有治陪着笑脸说道。
杨长礼瞪了他一眼,清清嗓子,继续说道。
以前吃的基本都是猪大油,家家户户都多少有点,沾到布上或草上,一点就着,再加上火从里面烧,自然不会被大雨浇灭,最后浇灭也晚了,里面都已经烧完了。
其它百户所的士兵过来之后,与正要撤离的倭寇又是一场大战,全歼倭寇,但是,我们的将士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之后他们将倭寇洗劫来的东西全部运回他们的所。
等我们老祖宗回来的时候,发现村子已经彻底毁掉,只好暂时住到堡垒里,战死的人各家找回去埋葬,不能辨认的,全部堆到深沟的角落里掩埋。
为了纪念百甲勇士,再遍植柏树,百通柏,有万古长青,千秋万代之意。那些倭寇的尸体也得处理掉,否则会引起瘟疫来,然后又将这些倭寇的尸体烧掉,剩余的零碎扔到臭水沟里。
为了方便祭奠这些战死的先辈,我们就在这附近居住,没有再回到原来的村子。
熊文远是芸㣮过来的,我们祖宗当年躲过倭寇的祸害,活下来的大部分都是孩子,活命大过天!就认他为义祖,为他立庙,塑身,逢年过节按时祭拜,所以我们既认晋阳洪洞大槐树是老家,又认芸㣮是老家,咱村的人去世之后,都是向西南方向指路,意思是先去芸㣮老家转一圈,认认义祖的门,感谢当年的活命之恩,使魂有所依,不忘根本,再回晋阳老家安魂归位。
杨长礼说着,抹抹眼泪,略一停顿,喝口茶,咕咚咽了下去,皱皱眉头,继续说道。
我们又在村子周围遍植松树,村名改为柏前村,意思是柏树的前边。在这方圆百里之内,唯有咱村松林成片,柏树参天,这都是有典故的。后来人口慢慢增加,村子也逐年扩展,深沟也一点点填上压实,再盖新房。
但是,这么多年过去,有些地方的阴气还是很重,因为当年死去的那些人,连副薄棺材也没有,最多就是用草苫子卷一下,大部分连草苫子都没分到,只能扔到深沟里埋掉,这叫居无所依,会产生怨气。
蓝星上有很多国家,华夏位于大陆东部。
咕河,是齐地半岛,蛟岽地区最大的河流,常年流水,起源于峊山西麓,流向西南,沿途有多条支流汇入,最后注入蛟洲湾。咕河上游山区,植被较少,水土流失严重。河口段受潮汐影响,天文大潮时进沙量大,形成淤积。
夏天汛期的时候,暴雨多出现在流域北部山区,洪水泄洪时,先占满河槽,使中下游平原排水困难而产生内涝,正因如此,中下游平原的土地非常肥沃,粮食产量比其它地方高,所以,从古代开始,咕河中下游两岸就聚集了大量的村落。
柏前村位于咕河中下游西岸,距离咕河堤坝不足百米。北边是一片古树参天的柏树林,东邻县道,县道往东到咕河堤坝是坟地,从县道到咕河河槽之间是一片南北长十余里的松林,其它的树木很少。柏前村有五千多人口,十几个姓氏,其中姓王的人家居多,我叫王兴逸,住在柏前村的东边。
齐地半岛蛟岽地区,虽说十年九旱,但是咕河在汛期时水量很大,来得快去得慢,所以咕河中下游地区的老百姓因地制宜,在咕河周围,开挖了很多河道和储水库,用来分洪或储水。在天气干旱的时候,也有水浇灌农田。同时,此地大部分地方地势平坦,土地肥沃,农作物的产量逐渐提高,人口得到极大的增长,原先数人的村庄逐渐变成百人,千人,与此相对应,房子也是越盖越多,逐渐向外扩展。平坦的地方都用来种植农作物或各种树木,不能随便盖房。这时,要盖新房的人家,就找村里批块凹地,自己雇人担沙运土,将凹地填平,沉淀几年之后就可以盖新房。
咕河西岸的柏前村就是这种情况,我家的新房子也盖在一条废弃的深沟旁边。为了使地基稳定,找人将深沟里临近盖房子的地方填平小半,深沟其它地方未动,原来什么样还是什么样。
据说,以前的时候,这条深沟是咕河上游的支流茱河的分支,流向与咕河基本平行,最后在柏前村南面三里的地方拐弯,流进咕河,后来不知因为何种原因,从茱河里岔出深沟的地方被填平,又将茱河连接咕河的那部分河道加宽,加深,从此以后,茱河里的水只流向咕河,不再流向深沟,深沟没有水源补充,水量逐渐减少,最后弃用,靠近深沟的村子都将深沟或多或少的填平了一部分,不再是一条完整的河流,连名字也被人忘记。
七十年代的时候,柏前村往南这段深沟还通向咕河,每逢大雨,积水沿着深沟流到咕河里,后来天气逐渐干旱,柏前村南边到咕河这段被彻底填平,深沟的排水功能消失,只在沟底有少量积水。因为这点积水的存在,深沟的里里外外长满各种灌木和杂草,其中以茅草居多,长的也最为茂盛。
新房西南边,十几米远的地方有一棵海碗粗细的的槐树,大概有二十多米高,长的笔直挺拔,枝繁叶茂。每年春天的时候,从上到下挂满槐花,老远就能闻到香味。当时,北方一些地方的国槐尺蠖泛滥,将树木的叶子啃食的干干净净,再结个茧吊在树上,称之为‘吊死鬼’,奇怪的是,这棵槐树的周围树木上都挂满‘吊死鬼’的时候,这棵槐树上一个吊死鬼也没有,还是枝繁叶茂的样子,连其它的虫类都很少见,而且也从未见到过树上有鸟窝。
在我十三岁那年夏天,正是天气最闷热潮湿的时候,北屋(老房子)狭窄,闷热,我和二哥被父母赶到南屋(新盖的房子)去睡觉。
那时,南屋刚盖好没多久,只用水泥打了地面,没有按窗户,也没有按门,更没有院墙。不是我的家人心大,南屋里除了水泥地上的两张凉席之外,还有一块长木板,两头用砖头支起来,上面是我的作业,另外再加几只蜡烛和蚊香,值钱的东西一点也没有,小偷也懒得光顾。
一天晚上,我半夜起来去院子外的沟边小便,正是月半的时候,月光还算明亮。朦胧之间,我看到那棵槐树上挂了好大一张草苫子,从树顶一直垂到地面,宽度比槐树还要宽一些,在月光的晖映下,草苫子显得白晃晃的。
草苫子是用麦秆或稻草杆编织的,大张的可铺到房屋的橼子上,再抹一层泥,上面盖上瓦片,挡风保温,冬暖夏凉。也可以挑选一些较长的麦秆,去掉叶子和外皮,清水冲洗干净,天气晴朗的时候,暴晒干透,再编织成与炕大小相同的尺寸,铺到炕上使用。或者做成八十公分宽,一米二长大小的草苫子,夏天去大街上乘凉的时候,往地上一铺,或躺或坐,既舒适又方便。
当时,我睡意朦胧,心里纳闷谁做了这么大一张草苫子。若是夏天用来乘凉,得多少人才能躺满这么大一张草苫子,而且这张草苫子的长度和宽度也远远超过屋面,因为房子上用草苫子我见过,是几块拼凑的,关键是这么大一张,想要挂到树顶,要不少人合作才行。
大槐树正对着的大门,是和我同辈的一个成年人的房子,叫王兴青。这棵槐树是他爹以前种的,王兴青对这棵槐树很上心,有人想要摘上面的槐花,必须经过他的允许,而且不能扯断大的树枝,摘下来的槐花,要留给他一半。要想将这么大一张草苫子挂上去晾晒,没有他的同意是不可能的,只要问问他,就知道是谁挂的。
我担心看错,又揉了揉眼睛,仔细看了一下,确实是一张巨大的草苫子,一动不动的挂在槐树上,甚至连上面的麦秆和草绳都看的清清楚楚,感觉就好像是挂在我眼前一样。
小便之后,我转身的时候,依稀看见远处平房上站着一个人影,一动不动的盯着这边,头顶上方隐约升起阵阵淡淡的烟雾,似乎时不时的有一点暗淡的红光亮起。我心里有点害怕,不敢仔细再看,赶紧跑回屋里,拖着凉席往我二哥那边靠了靠。侧身躺在凉席上,竖起耳朵仔细倾听外面的动静,可是除了听到各种虫鸣的声音之外,我什么也没有听到,过了一会儿,睡意渐渐袭来,我迷迷糊糊的沉睡了过去。
半梦半醒之间,我做了一个梦,发现自己身处一个穿古代衣服的朝代,自己是乡下一个编织草苫子的小贩,每天辛苦劳作,连个温饱都混不上。所以,每天下午吃完饭之后,我开始编织草苫子,一直工作到半夜,然后将所有的草苫子打包放到独轮小推车上。天不亮便起床,用独轮小推车推着草苫子去集市上贩卖。有一次,我走到半路的时候,发现邻村新开了一个集市,赶集的人很多,比我经常去的任何一个集市的人都多,我抱着试试的态度,将草苫子推到集市上售卖。没想到,我刚停下,还没有开始吆喝,赶集的人便围了过来,纷纷要买草苫子。
我便报了一个比平时稍高的价格,意外的是,这里的人根本不讲价,要多少钱就给多少钱,但是也不多买,每人就买一个,买完就走,也不看草苫子的质量。卖光之后,那些没有买到草苫子的人跟我说,他们这里每天都有集市,最缺的就是草苫子,催促我赶紧回家编织,有多少要多少。于是,我每天下午编织草苫子,第二天一早拉到集市上卖。更奇怪的是,整个集市就我自己一个人卖草苫子,再无第二家,这种情况大概持续了几年的时间,直到有一天,我的草苫子突然一个都没有卖掉。从那天开始,无论我在集市上如何吆喝,再也没有人来买我的草苫子,我越来越烦躁。
正在急得无计可施的时候,有人猛推了我一把,我一下子从梦中醒过来。
“赶紧起床,回家吃完早饭去地理干活。”
我这才发现,天已经大亮。我缓了缓神说:“昨天晚上,半夜起来小便的时候,我看见青哥门口的大槐树上挂了一个大草苫子,从树顶一直伸到地面,是做什么用的。”
二哥疑惑的说:“什么大槐树上的草苫子,我一早就去前边压水浇菜园,没看见,你睡迷糊了吧。”
“不可能,昨天晚上我亲眼看到的,怎么会没有,会不会是清早被人给,收走了。”
我急忙爬起来向院子冲去。果然,大槐树上什么也没有。
难道一早就被人收走了?我不禁有些疑惑。
这时,二哥过来说:“你应该睡迷糊了,这么大一张草苫子挂在树顶上,用什么撑起来?”
然后催促我赶紧回北屋吃饭,吃完饭去地里干活,趁着下雨之前,给玉米地施上肥料。
傍晚的时候,我和二哥又到南屋睡觉,正好青哥过来串门。
我说起槐树上的草苫子的事,王兴青摇头说,这绝对不可能的事,根本没有人做草苫子挂在槐树上晾晒,白天没人挂,晚上更不可能挂,两人将我一顿嘲笑,转开话题去说别的事情。
我在一旁插不上话,听了一会儿,甚觉无趣,去村里找同伴到咕河里洗澡。
八十年代初期的时候,刚温饱没有多久,物质比较匮乏,刚通上电,没有什么电器,热水器更是稀罕物,根本没听说过,想要洗澡,只能去咕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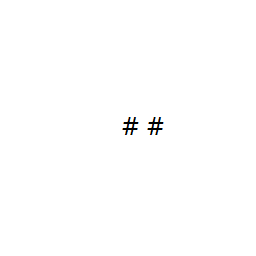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