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女主角分别是抖音热门的其他类型小说《那个叫做老家的地方无删减+无广告》,由网络作家“扫院小僧2317”所著,讲述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故事,本站纯净无弹窗,精彩内容欢迎阅读!小说详情介绍:着父母一起周边逛逛,总是觉得陪伴父母的时间太少,但是现在农村的现状让父母也觉得待久了平淡无味,他们曾经的同龄人要么不在家要么不在了,白天的无聊夜晚的寂静给他们的感觉不再是宁静而是孤独,这种感觉是有一次和父亲通话时感受到的,当时通话父亲说起比父亲小两岁的邻居xx死了,我当时只是感叹邻居年纪不算很大,但是感觉父亲却更加伤感,事后我思索了一下发现了事情原因,邻居不仅是邻居更是父亲小时候的玩伴,在那个没有电视娱乐的年代没有比同伴之间的玩耍更快乐的了,年老的人不一定就需要安静,可能他们更怕孤独。三天四夜一晃而过,因为是晚上10点的飞机,我本想下午7点再走,离别总是不舍,但是父母一直催促我早点出发。下午四点半在我回来的时间点,在落日余晖下,我再...
《那个叫做老家的地方无删减+无广告》精彩片段
着父母一起周边逛逛,总是觉得陪伴父母的时间太少,但是现在农村的现状让父母也觉得待久了平淡无味,他们曾经的同龄人要么不在家要么不在了,白天的无聊夜晚的寂静给他们的感觉不再是宁静而是孤独,这种感觉是有一次和父亲通话时感受到的,当时通话父亲说起比父亲小两岁的邻居xx死了,我当时只是感叹邻居年纪不算很大,但是感觉父亲却更加伤感,事后我思索了一下发现了事情原因,邻居不仅是邻居更是父亲小时候的玩伴,在那个没有电视娱乐的年代没有比同伴之间的玩耍更快乐的了,年老的人不一定就需要安静,可能他们更怕孤独。
三天四夜一晃而过,因为是晚上10点的飞机,我本想下午7点再走,离别总是不舍,但是父母一直催促我早点出发。
下午四点半在我回来的时间点,在落日余晖下,我再一次出发,母亲去串门了,母亲的记忆力有点差,总能记起陈年烂谷子却想不起来我哪天回来,哪天回家,父亲不让我告诉母亲我要走了,我同意,四年前,我开车拉着老婆孩子走的时候从反光镜里看到母亲在抹眼泪,我不想看到母亲在送我的时候再抹眼泪,父亲还是送到胡同口,我打开车窗扭头道别,同时深深地吸了一口故乡的空气,将它铭记在心底,二十多年前的老家已经篆刻在记忆深处,永远不会磨灭,我想把现在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印在脑海中,车行至路口马上就要拐弯,从反光镜里看到父亲仍然立在原地,我得眼泪流了下来。
我知道,无论我走到哪里,老家永远是我心中的那片净土,是我灵魂的栖息地。
回老家除了看望父母亲人,还有对最美好年少时光的追忆,也许在老家待上三天你就觉得平淡而无味,但过了半年你又开始想他了。
锅浆糊干什么?”
,我当时那个尴尬,忙解释说“这是我们老家特产”,之后数年每每提及此事都会被他们嘲笑一番。
现在生活好了煮稀饭时候放上各种米、豆之类叫做“粥”,我喜欢煮红薯,所以每次回老家都会标配“红薯糊涂”。
吃过晚饭和父母看着电视聊着天,从时事政治到家长里短,从村东头到村西头,说一些新鲜事也叙一叙陈年烂谷子,每次都是母亲催促方才结束。
等他们躺下,我便一个人来到院子里感受些凉风,这一刻城市的喧嚣与纷扰已经远去,心中满是宁静与安详,邻里邻居已没有几户人家在家,晚上再听不到四处的狗吠鸡叫。
村里有多少户、多少人,我一直没搞明白,只知道村里分了五、六、七三个生产队,我们家是七队,而一、二、三、四四个队在哪里我也是近几年才知道,原来我们三个自然村合为一个行政村,那两个自然村平分了四个队,而我们村独占了三个队,小时候一直觉得村子挺大,印象中从来没有跑遍过全村,现在想想这不仅与地域有关还和人口有关,那些年和我同龄的人很多,单单我们七队上下几岁的同龄人男男女女二三十人,上学放学在一起玩就得分帮分组,根本无暇再去跑遍全村别的队找人玩,等到上初中时开始同学之间串门这才跨区域活动稍加频繁,慢慢的上了高中,人群开始了第一次大的分化,不少初中毕业不念书的开始陆续外出打工挣钱,接受社会的磨砺和锤炼,在一起的时间少了,偶尔碰上话题更加丰富距离却越来越远,更多的交流在几个读高中的同学之间,不过那个时候每月休息一次,一次在家待上一天两晚上,充其量也是半天时间凑在一起谈谈学校谈谈老师谈谈哪个公认的漂亮女生,就是不谈学习。
那时候街上还是热闹的,我们十五六岁还是小孩,我们的父辈四十来岁正当年,天热的时候邻里邻居还会各自端着饭碗来到街上边吃饭边聊天,天南海北鬼狐精怪,畅所欲言,没人去核对真假对错,只图一乐。
如今三十年过去了,大街犹在街两旁的房子高了,大街显得更窄了,街上的人却少了,当初的小姑娘早就嫁了,当初打工的依然在
,回老家时间总是有限的,老家房子坚固能住就行,没必要和别人比,毕竟盖房子也是劳心劳神的事,句句在理。
在我的概念里老家的房子已经不仅是居住的功能了,他更是我深藏于内心的记忆和牵挂,真要哪天突然变成高楼大厦了总感觉那不是家了,弟弟的想法和我略同。
就这样老家的样子一直深藏在我的记忆里没有变过,只有一点母亲抱怨了好多次,就是院里那棵香樟树,我在四年前回来的时候那棵树还像婴儿的手臂粗细,两米来高,枝叶茂密而不张扬犹如伞盖,凑近一闻能感受的清香,如今这棵香樟树已有碗口粗细,只不过前些日子让大伯修剪树枝,大伯把整个树枝全部剪掉了就剩下一个粗壮的树桩扎在泥土里,院子里少了些许绿色,我安慰母亲说道:“只要有根在,慢慢的总会发芽的变绿的”。
我一个人回老家都是母亲来做饭,我不但不动手,反倒有一种心安理得的感觉,我感觉母亲还能做说明母亲还没老,母亲爱干活干了一辈子对此也乐此不疲。
吃饭很简单,早晚是红薯稀饭,老家又称为红薯“糊涂”,锅盔加炒菜,锅盔以前都是母亲自己用平底锅炕的,现在多半买着吃,炒菜就随机了,有啥吃啥。
关于“糊涂”我得多说几句,在我们当地,以前开水不叫开水叫“茶”,煮稀饭的时候不管稀饭煮的是大米、小米还是红豆、红薯等等只要最后水开不冲上面糊,那一律叫“茶”,如果是煮米的就可以叫“米茶”,只有冲上面糊了才叫稀饭,小时候穷村里做稀饭什么也不煮,白开水烧开了冲上面糊就叫稀饭,又叫“糊涂”。
记得2005年刚上班的时候,有一天下午单位大家都在忙碰巧厨师请假了,领导在饭店定了几个菜,末了安排我这个最小的小青年去煮稀饭,我欣然应诺用河南漯河传统手艺炮制了一锅稀饭,凑巧那天忙的比较晚,等去吃的时候领导死活找不到稀饭,我很诧异我明明煮了一锅的,我忙跑到厨房掀开锅告诉他稀饭早已搞定,领导看着一锅稀饭差点没笑喷出来说:“我掀开锅看了两遍没敢认,让你煮稀饭,你怎么整了一锅浆糊?
我们几个想来想去都没想明白你整这
我住在山东威海,我的老家在河南漯河,这一海一河相距一千公里。
我已经四年没有回老家了。
前三年是因为新冠疫情的原因,去年是因为父母居住在河南鹤壁,我的时间、孩子的时间要凑上父母的时间才好,凑来凑去不合适又滑过了,回老家看看的想法一直萦绕心头。
今年三月中旬父母要回老家住住,我决定不再凑时间自己先回家看看。
下午两点半下了飞机,联系租车公司办理车辆交接手续,设置导航开始自驾回家之旅,心中涌动着难以言表的复杂情感,那是一种交织着熟悉与陌生、亲切与感慨的独特体验,两个小时下了高速转入省道、县道,窗外的景色由灰黄渐次转为嫩绿,大片大片的麦田一眼望不到头,这在威海是完全看不到的。
现在但凡出门我几乎是完全屈服于导航,跟着导航走街串户,不知不觉中一些脑海里曾熟悉的地名出现在路牌上,我知道家近了,心里一下子踏实了。
田间掠过一些桃树、油菜地,桃花只是露出点粉白,油菜花已经盛开了,一片片淡黄,不仅在田地里,路旁的小沟沿,谁家院落的门口散落着,一股股清香飘入车内,淡淡的有点甜,沁人心脾。
我索性降下车速把车窗打开,任由凉风裹挟着泥土味和花的清香吹进来,那是故乡的味道让人沉醉让人舒畅。
走到村口的时候正对着夕阳,通红的夕阳宛如一个巨大的火球悬挂在天边,火球的周围散发着金色的光芒。
远远的望见父亲像往常一样在房后的胡同口等我,他的影子在夕阳下拉的很长,我的心中顿时满是愧疚,虽然每周都会和父母电话、视频,但网络终究是虚拟代替不了现实,只有在身边才会心安。
车停在家门口原来的地方,家和以前一样,正房是青砖蓝瓦的四间瓦房,带一个院子,院子的东侧有两间厢房用做厨房,院子西侧有菜地、洗漱间和几棵果树,几十年几乎没有变过。
只不过老式的瓦房在东西邻居楼房的映衬下就像一个窝棚。
关于房子父亲也有过拆了重修的想法,但这个想法一说出来就被母亲否决了,我和弟弟知道后投了中立票,但实际意见也是否决票,母亲的意思主要是我和弟弟都在外地安家落户
磙转动,麦粒从麦穗上脱落下来,这叫“碾场”,碾上几遍后把麦秆翻过来再碾几遍这叫“翻场”,碾完后麦秆变成了麦秸,把麦秸垛成堆存放以后用来烧火做饭,把麦秸清理干净后剩下的就是麦粒了,但是这时候的麦粒并不干净里边还有没完全脱离的麦皮,这就需要用木掀将麦粒扬起来让风把麦皮吹走这样留下来了就是相对干净的麦粒,这个过程叫“扬场”,这个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灰尘,人们往往灰头土脸,但丝毫不在意。
只有这个过程结束了小麦装袋归仓,收麦才算告一段落。
整个过程看似不复杂但真要干完颇费时间,麦收时间少说要持续一个来月,要是遇到下雨天那就更麻烦了,地面湿滑不能碾场就只有等,等到天好了麦场干了能碾场的时候才能继续进行,要是等久了割完的麦子就会生芽,这被称为“塌场”,麦收时节最怕“塌场”。
而我最怕的是捡麦穗,麦子在地里收割完后难免会有掉落在地上没有收到打麦场的,本着颗粒归仓的原则就需要重新去地里捡一遍,捡麦穗是有讲究的,要趁着早上地里有潮气的时候去捡,等到天亮了天气热,麦穗发干易断不容易捡,于是早上四点来钟就要爬起来,我每次都是被揪着耳朵硬拽起来的,眼都睁不开的时候一手拎着袋子一手机械性的捡麦穗,父亲在揪我捡麦穗的时候总是会说“不好好学习以后只能干这个,咱家那辆架子车留给你”,我就是那时候被干活吓坏了才一直没提出放弃读书,后来直到我念警校的时候一到麦收季节我都会打电话给家里问今年有没有“塌场”,那时候母亲告诉我现在有了联合收割机,直接把麦收时间由一个月缩短到十天了,后来联合收割机普及了,麦收时间直接缩短到三天,到毕业工作之后就再没问过“塌场”这事了,现在“碾场扬场”这事成了历史,同样热火朝天抢收抢种的劳动场面也消失不见了。
父亲很诧异这么多年了还知道收麦的情况这么清楚,我笑而不答,三十年前的记忆早已镌刻在脑海里,没有任何东西能掩埋掉。
我自从结婚后基本就断了狐朋狗友的联系,回老家很少出门去玩,即便出去也是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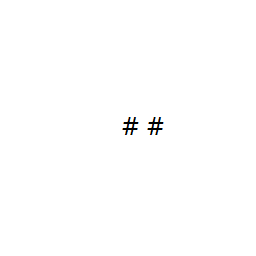
最新评论